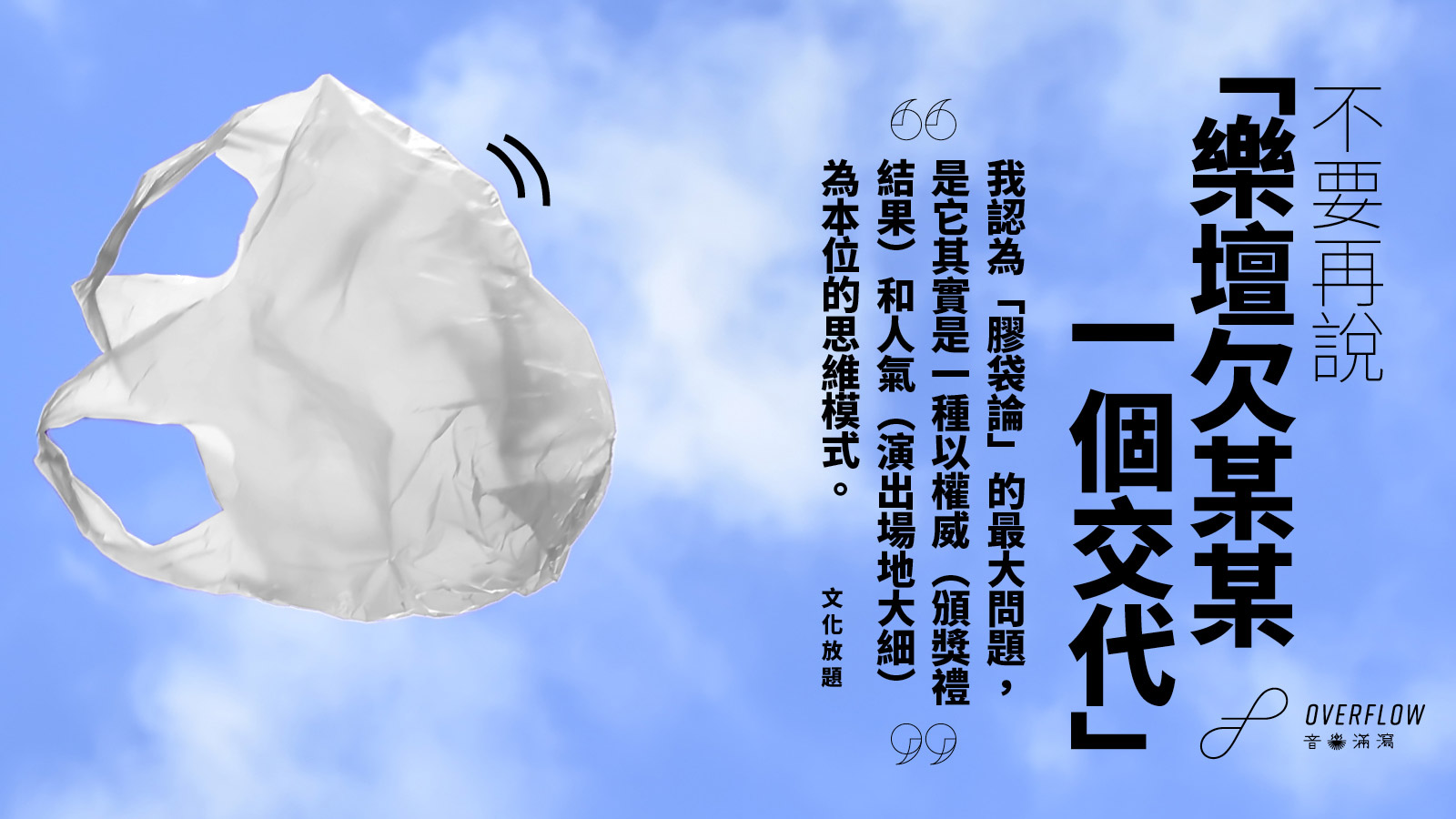音樂只是手段?
我認為「膠袋論」的最大問題,是它其實是一種以權威(頒獎禮結果)和人氣(演出場地大細)為本位的思維模式。一來,縱然樂迷每每亦是抱住一種「自己鍾意嘅嘢攞到獎 = 獎項有公信力」的主觀投射,但客觀地從機制與獎項設計的角度而言,各大頒獎禮的認受性根本早成疑問;二來,用人氣、獎項這些與音樂未必完全有關的事(例如很多歌手的人氣主要來自影視而非音樂,同時不少音樂獎項説穿了亦只是人氣大獎)作為衡量某個 artist 成就以及是否得到充分「交代」的最大標準,這是否有點兒太過本末倒置?
C AllStar 七年前的《生於斯》是他們頗為上乘的一隻概念大碟,但裡面的〈紅館夢〉卻是我打從心底地討厭的一首作品。歌曲以音樂夢為題,然而遠比他們純粹更多的前作〈我們的胡士托〉,黃偉文筆下的「音樂」幾乎在每句都淪為了獲取名氣、獎項甚至他人景仰的手段——尤其聽到「要唱到我的肖像/榮登於隧道口每面牆/仍能毋忘初衷唱」那句,我直頭想直接吐血而死。
當然啦,個別的作品不足以代表 artist(尤其短暫休團後的 C AllStar)最真實的心態。然而這令我想,當我們不斷為那些本來或許只為興趣、為藝術、為自己而做音樂的人搖旗吶喊、聲討各種「交代」的時候,我們會否變相在鼓吹著一種(如〈紅館夢〉的歌詞般)將音樂視為「手段」而非「目的」的功利文化?
音樂作為目的使人自由,但作為手段就會使人毫不自由。假若一個 artist 需要得到最佳乜乜乜的獎項、過十百千萬人的掌聲,才會感到自己的努力並非徒然,那麼音樂對他而言,恐怕本身就沒有太多自足的快樂和意義。反之,假若音樂就是目的、創作就是意義,就算沒有獎項、未有掌聲,那又怎會有種自己正在受苦的感覺?若然 artists 從來都早已樂在其中,粉絲們、歌迷們又何用時常千方百計地、大灑金錢地(甚至不擇手段地)不斷強行地為他們製造更多膠袋?